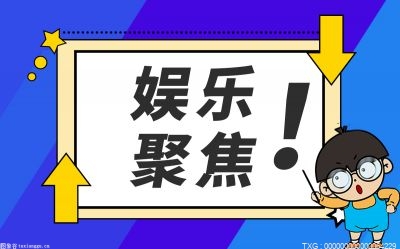试管作为助孕的一种医疗手段,耗时长,过程繁琐且价格不菲,但对于渴望孩子的家庭来说是唯一的希望。青岛的杜女士此前就因不孕来到了青岛首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首大医院)进行检查、打了促排针,并在该医院介绍下,来到合作医院进行试管助孕。不过可惜的是,因卵泡流失最终杜女士错失了受孕时机。而在此后,杜女士发现青岛首大医院并无试管婴儿及辅助生殖的资质,给其检查及打促排针的做法属于开展试管婴儿的辅助工作,涉嫌无证行医。为此,她将青岛首大医院及合作医院上海同济医院告上法庭。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患者不孕来到医院做检查打促排针
2018年8月,婚后一年未孕的杜女士来到青岛首大医院检查住院治疗,并在医院进行了腹腔镜下盆腔黏连松解术、左侧输卵管系膜囊肿解除术、宫腔镜检查术等多项手术,于2018年8月12日出院。
出于对医院的信任,此后,杜女士为治疗不孕不育多次到青岛首大医院就诊,并在该院的协助下,于2019年11月和2021年5月先后二次到上海同济医院就医,希望进行试管助孕,但均未成功。
杜女士称,第一次试管助孕失败源于两医院未告知应注意事项和出现遗漏环节导致没能取到卵。而在之后,她发现青岛首大医院并没有做试管婴儿资质。“没有资质,却为我和丈夫进行检查、打排卵针等试管婴儿前期准备,这等同于进入做试管婴儿流程程序,构成非法行医。”
此外,杜女士认为上海同济医院在明知青岛首大医院没有做试管婴儿的资质,却让青岛首大医院协助做试管婴儿前期准备工作,也有过错。
据悉,杜女士因试管助孕等系列检查,所花费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共计89213.48元。为追回损失,她将青岛首大医院及上海同济医院同时告上法庭,并索赔精神损失赔偿金1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杜女士及丈夫主观上认为上述两家医院均有过错,但对于其医疗行为是否真实存在过错,并未申请进行司法鉴定。
两医院主张医疗行为无过错
对于杜女士的起诉,青岛首大医院和上海同济医院则认为其医疗行为并无过错。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患者到医院就医,医院并不能保证100%治疗好患者的疾病,故患者杜女士到医院治疗未能怀孕的事实,不能据此认定青岛首大医院、上海同济医院违约,进而要求两医院退还全部医疗费用并赔偿损失。
其次,法院认为杜女士及丈夫主张两医院过度医疗、违规行医,造成损害,但拒绝对两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申请司法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法院表示,医疗机构是否构成非法行医,应以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认定为准,对于青岛首大医院协助上海同济医院进行试管婴儿的辅助医疗,是否构成非法行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做出判断。
综上,驳回当事人杜女士及其丈夫退还医疗费并赔偿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诉求请求。
二审维持原判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
对于一审判决,杜女士一家不服,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并在二审审理期间,主张两家医院违反告知义务。一方面,杜女士认为,青岛首大医院对于其此前手术原因、目的、方案及打促排针后的取卵时机、何时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等未告知。另一方面,杜女士认为,上海同济医院对于其身体是否适合取卵,能否正常取卵?其无法正常取卵原因,后续的治疗流程、方案等事项未进行告知。
而对于杜女士的主张,青岛首大医院否认开展过任何试管婴儿、辅助生殖的诊疗行为,不存在杜女士口中的“非法行医”行为。并主张为杜女士注射促排卵针并非开展试管婴儿的辅助工作,仅为一般注射行为,杜女士属于错误混淆辅助生殖概念,强行将注射促排卵针行为与辅助生殖工作划等号。此外,青岛首大医院表示从未给予杜女士任何承诺。此前给杜女士进行的相关手术及诊疗行为也均为其本人签字同意,且检查为自愿行为。在拿取报告时,医生也明确告知了其身体情况,不存在未告知等违约行为。
而另一方上海同济医院在法庭上则表示,曾告知患者杜女士列举的各项疑问,并表示试管失败是源于其卵泡生长不良从而放弃治疗,也因此并未进入试管婴儿建档案及取卵等试管婴儿助孕后续程序,因此谈不上什么风险告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关于两医院是否违反告知义务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患者来举证。中院表示,患者杜女士在二审中确实列举了两医院诸多的告知义务并主张两医院未履行告知义务,但根据青岛首大医院检查单明确记载的各项指标及《宫腔镜手术知情同意书》,上海同济医院提交的与患者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法院认为上述两家医院并不存在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
此外,结合杜女士拒绝对两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申请司法鉴定,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青岛首大医院构成非法行医的情况,青岛中院认为当事人杜女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驳回杜女士及丈夫赵先生的再次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信网记者 顾青青